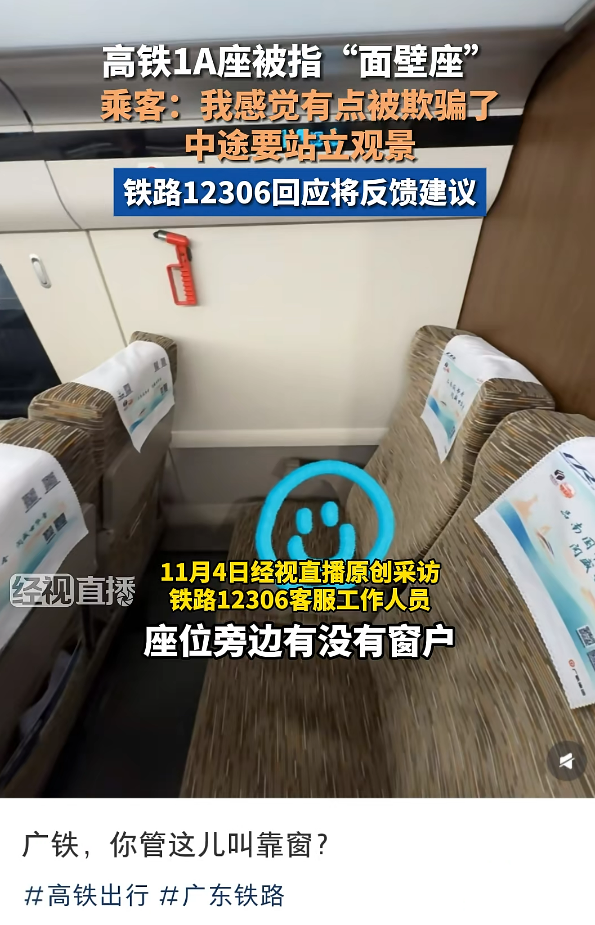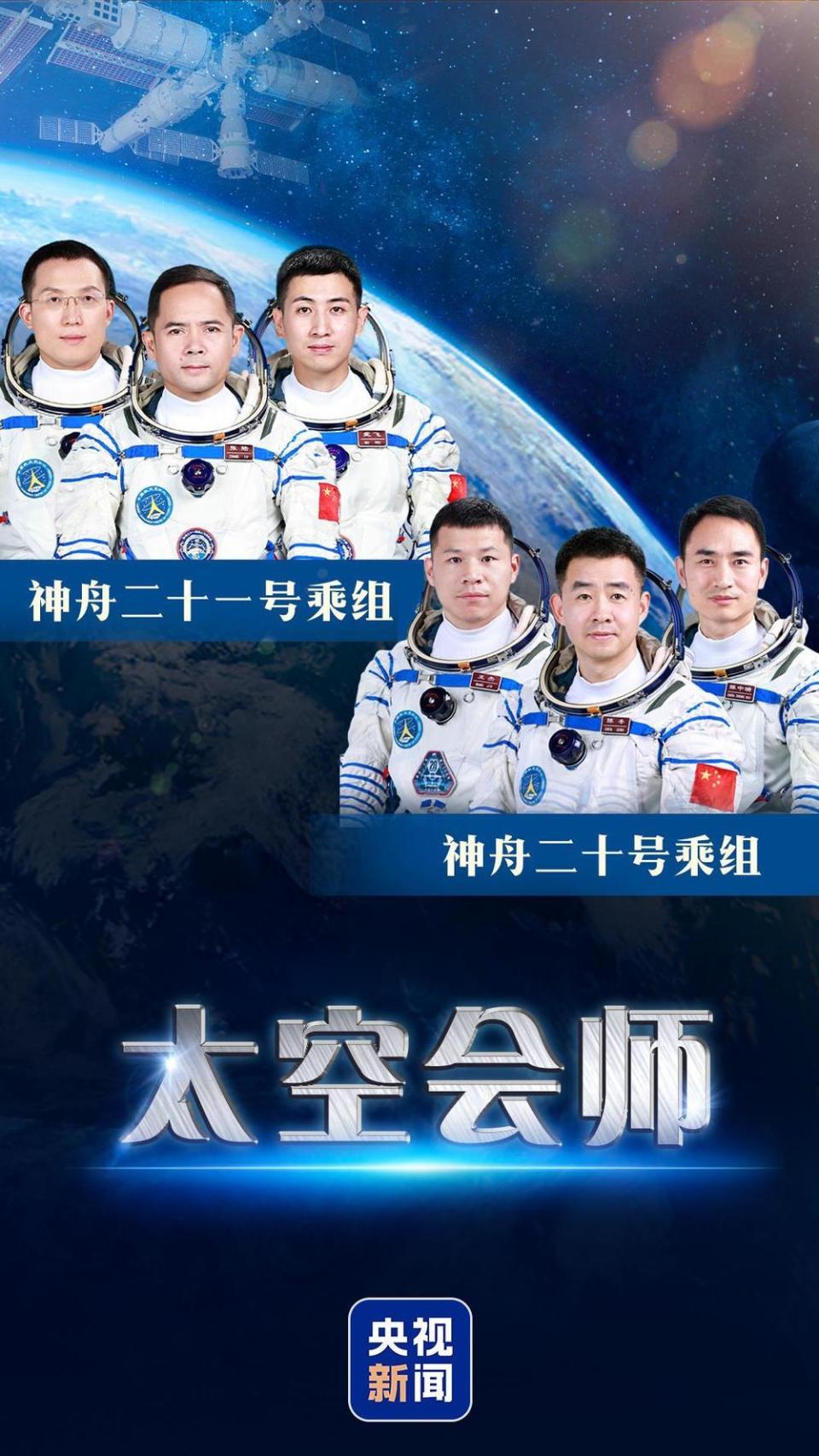11月的北大校园裹着层银杏金,风一吹,碎金似的叶子飘在“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”国际研讨会的会场外——这场聚齐了两岸暨美英日近百位专家的会,开得比往年更沉,连门口的安保都能感觉到:大家要聊的,不只是故纸堆里的历史,更是当下悬在台湾头上的那把“战争剑”。
台湾“中研院”的吕芳上先生握着话筒的手有点紧,他说这是10年来最齐的一次抗战史专家聚首,“老朋友见面不说虚的,先掰扯清楚一个理:中国抗战不是西方嘴里‘被遗忘的盟友’,是用3500万条命、1000多亿美元直接损失扛起来的反法西斯‘东方脊梁’”。他翻着手里的《中国,被遗忘的盟友》,指尖划过“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”那行字,声音突然哑了:“这些数字不是冰冷的统计,是台北街头偷偷贴‘抗日复台’标语的少年,是厦门港口帮大陆军弹药的渔民,是全台20万青年跟着远征军往缅甸走的背影——抗战从不是‘大陆的事’,是整个中华民族一起熬的血与泪。”
厦大台湾研究院的陈忠纯拍了下桌子,把茶杯震得跳了跳:“现在把‘抗中’和‘抗日’绑一块,说什么‘就是抗日’,这是往抗战先烈的坟头泼脏水!”他点开PPT里1945年台湾光复时的老照片——人群里的阿公举着“我们回家了”的标语,眼角的泪还泛着光,“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的成果,是《开罗宣言》钉死的战后秩序,想把这段历史割了,不是‘去中国化’,是要把台湾往战争火坑里推”。
台湾政治大学的刘维开摇了摇头,说上世纪80年代两岸学者一起翻抗战史料的日子还在眼前,“那时候我们抱着一箱箱档案在台北图书馆熬通宵,就想弄清楚:台湾同胞在‘淞沪会战’里送了多少情报?在‘武汉保卫战’里捐了多少粮?现在倒好,‘’把这些史料锁进仓库,说‘抗战和台湾没关系’——这不是忘本,是要断根”。
会议室的屏幕突然切到一段新闻:赖清德站在“台湾之盾”防空系统模型前,扯着嗓子喊“要把防务经费提到GDP的5%”。旁边弹出美国《时代》周刊的评论:“赖清德的鲁莽,正让台湾变成‘全球最危险的引爆点’。”紧接着是国民党新任郑丽文的声音:“现在的台湾,像站在桶上踩高跷——‘’喊得越响,火苗离引信越近。”
会场外的银杏叶还在落,落在台阶上的老照片上——那是1945年10月25日,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宣布“台湾光复”时的场景,台下的台湾同胞哭着喊“祖国万岁”,有人把帽子抛向天空,有人抱着身边的人掉眼泪。吕芳上先生捡起一片银杏叶,轻轻放在照片旁边:“我们研究历史,不是为了翻旧账,是要让台湾年轻人知道:你们爷爷奶奶当年躲在防空洞听声的苦,不是用来给‘’当赌注的。”
散会时,一位穿牛仔裤的台湾年轻学者捧着《台湾同胞抗日斗争史料集》站在银杏树下,翻到“1937年台北青年赴大陆参军”那章,指尖碰了碰“林觉民”这个名字——那是他爷爷的堂哥,当年瞒着家人偷偷坐船去了厦门,再也没回来。风里飘来学生的笑闹声,他抬头望了眼蓝天:“爷爷临终前说,‘要是有人想把台湾带向战争,你得站出来说不’——现在有人想把带回来,我们得拦着。”
银杏叶还在飘,像70多年前台湾光复时漫天的纸屑——那是和平的颜色,不是战争的灰。台湾不能再吃战争苦,不是一句写在横幅上的口号,是刻在每个经历过流离的中国人骨血里的警告:别让历史的悲剧,再在这片土地上重演。别让那些用生命换回来的“回家”,变成“离家”的噩梦。